美国和加拿大主要接种的是辉瑞-拜恩泰科(Pfizer-BioNTech)和莫德纳(Moderna)的疫苗。其背后关键技术都是mRNA。这两种疫苗有效率高达94%以上,mRNA 疫苗因此也被认为是美国和加拿大新冠疫情终结者。
这得归功那个66岁的老太太,匈牙利裔美国女科学家卡塔琳·考里科(Katalin Karikó)。如果没有她,也就没有mRNA新冠疫苗。
为这一天,她等了40多年。
莫德纳, 拜恩泰科,股价暴涨,投资人赚得盘满钵满,狂赚上亿,而考里科的分红只有300万美元。
对于这巨大的利益差距,考里科毫不在意,一笑置之。”还好。我只是喜欢我的工作,相信它的所有可能。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长,能看到我的作品结出果实。”

她的年薪,至今没超过6万美元。苦熬40年,她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希望,死路一条。没有科研经费,被解雇,被驱赶,被降职,被像虫豸一样遭到嘲笑和羞辱,是她40年的家常便饭。这点落差,真不算什么。
来自屠夫家庭
“我是在一个没有自来水、没有电视、没有冰箱的房子里长大的。这是我生命中的前十年。我甚至不知道还有其它的生活方式。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。”
1955年10月17日,考里科出生在匈牙利南部一个名叫萨拉什的小镇。他们只有1个房间。标准的穷苦人家。爸爸是这个只有一万人口小镇上的屠夫。

帮亲爹杀猪打下手,就是她的日常。不过,这个快乐的女孩,生性好奇,喜欢观察动物内脏,研究屠刀下生物的构造。生物学的兴趣自此产生,从此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,尽管她从未见过科学家。
从小学到大学,考里科一直很喜欢生物学课程。高中时,她曾获得首届杰尔米•古斯塔夫最佳生物学学生奖;大学时的她也曾获得过奖学金。1978年大学毕业后,考里科继续求学,并在塞格德大学(University of Szeged)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。随后,考里科在匈牙利科学院(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)下属生物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。

研究新技术被开
早在1961年,科学界发现,在DNA和蛋白质之间有个“中间人”——mRNA负责传递信息。理论上说,只要控制mRNA,就能命令细胞只生产特定蛋白质,就可以制造自己的“药物”,从而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疗法。
考里科参与一项临床试验,对一些艾滋病、血液病等患者进行双链RNA治疗,查阅了大量mRNA的资料。偶然间接触到的概念,一下子就迷住了她。她坚信mRNA可以成药,用来抵抗疾病。
不过,要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应用,要难得多。几年下来,考里科没能突破。还因痴迷mRNA,没有别的成果,被单位开除……这是她30岁的生日礼物。
上个世纪80年代,考里科身边很多同事都想去美国工作、生活。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,她并不想离开祖国。不过,这里似乎没有给她很多就业机会。失去工作的她,不得不远赴美国,接受天普大学(Temple University)提供的工作机会。
泰迪熊里藏了一千两百美元
1985年,考里科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匈牙利前往美国。为凑盘缠,考里科破釜沉舟。她卖掉自家汽车,将在黑市上换的1200美元缝进2岁的女儿苏珊的泰迪玩具熊里(当时匈牙利政府只允许他们带走100美元)。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身家。

到了美国,谁也不认识,还有些语言不通。千辛万苦,大洋彼岸的美国梦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好。
那段时间,研究mRNA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,但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致命难题:mRNA在到达靶细胞之前,会被人体的防疫系统破坏,简单的说,就是mRNA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。
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,大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。在当时看来,mRNA的成药性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科学界都认为改造DNA是治疗遗传疾病“一劳永逸”的办法。
考里科却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mRNA上。读博时期她便认为mRNA在治疗疾病上更有潜力,在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中她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。然而她博士后的老板并不这样认为,在一次大吵之后,考里科差点要被驱逐出境。没有科研经费,没有研究团队,她陷入绝境。

此时隔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递来一根救命稻草。1989年考里科离开天普大学,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。新的职位为研究助理教授,比原先的降了好几个级别,比副教授还要低一些,几乎就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职。
也就在这份工作里,考里科迎来了一次不小的突破。她与人合作,将mRNA导入到细胞中,成功地合成了mRNA编码的蛋白!这也就意味着,也许可以使用mRNA来改善心脏搭桥手术的血管,甚至还可以使用该技术来延长人类细胞的寿命!
遗憾的是,当时对mRNA的研究已如“一潭死水”。考里科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被看好,也没获得业内关注。
被逐出实验室
1990年,考里科提交了第一个mRNA治疗申请,希望获得资金来进行开发,却被拒绝了。用mRNA作为治疗方法,在那时看来是被认为是过于激进的,财务风险巨大。所有的投资机构都对考里科说了“不”。
“我一直在想办法改进技术,寻找更好的RNA、更好的递送方式。” 考里科知道当时设计的mRNA会引起小鼠体内的炎症反应、危及健康,所以要想办法让mRNA“欺骗”机体免疫机制,让它认为mRNA不会对机体造成伤害,这样才能提高mRNA成药的机会。
为此,考里科整天泡在实验室里,常常是从早上6点一直研究到深夜,甚至睡在办公室里,周末和假期也是如此。她说:“在别人看来,这似乎很疯狂、很挣扎,但我在实验室里很高兴。用我丈夫的话说,’这是给你的娱乐’。我觉得自己不是在上班,而是在玩耍。”

不过,考里科对mRNA的研究热情,并没有非常快地转化为“看得见”的成果。加之当时科学界对mRNA的认识一直停留在“极为困难”的阶段,没有人愿意资助考里科继续研究。
“我试图申请获得政府资金、投资者的私人资金等等,但每个人都拒绝了。”
199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决定将考里科降职。在被降职后不久,考里科被诊断出患上了癌症,她的丈夫因签证问题被滞留在匈牙利。此时的女儿正在读书,还需要钱来支付学费。
“通常在那时,人只会说再见然后离开,因为太可怕了。” “我想去别的地方,或者做别的事情。我以为是我不够好,不够聪明。”
迟迟未等到的资助、猝不及防的癌症、不在身边的家人,似乎每一件事都在问考里科:还要继续研究mRNA吗?
躺在病床上的考里科最终还是给出了“YES”这个答案,仍然坚持十几年来坚持的研究。这一次的抉择也决定了mRNA后来的发展。
考里科说,”宾大的前主席对我的态度很糟糕,一度把我赶出了实验室。他告诉我,我可以去动物园附近一间小屋,作为我的实验室。”
考里科在被降职后要求宾大的新主席恢复她以前的职位,却被告知她不是 “教员的料”。
她只能从一个个高级科学家的实验室辗转,变为人手不够时的“替补”,彻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。
复印机前的一次偶遇,得到了第一笔经费
没经费,考里科连最新的学术杂志都看不到,只能自己复印。这才有了学校施乐复印机旁的奇遇。她遇到了 “贵人”、免疫学家德鲁·韦斯曼(Drew Weissman)。
“那天我正在扫描东西,韦斯曼博士正好也在,我向他介绍,我是一名RNA方向的科学家,我目前着力在研究信使核糖核酸mRNA在疾病预防方面的前景。”
“万万没想到,韦斯曼博士也告诉我,他正在想研发针对HIV艾滋病的疫苗,或许需要利用携带特定遗传信息的mRNA来诱发人体产生特定病毒蛋白。”

考里科表示,那一刻仿佛遇到了“天选之人”,自己就如同在婚礼上激动的新娘,连声说道:“Yeah, I do, I can do it!””我是一个RNA科学家,我可以用mRNA制造任何东西。”考里科说。
韦斯曼博士一听顿时来了精神,立刻决定资助她!
两人成为合作伙伴。
1997年,考里科熬出了头。拿到第一笔经费,10万美元。

有了这笔钱,项目渐有起色。
8年后的2005年,他们终于找到解决人体免疫反应的办法,用弱化的版本替换了一个RNA的模块。
这样,人造的mRNA,就像神偷一样,不知不觉的潜入人体细胞,而不会惊醒人类的免疫防御系统。
“mRNA能用于改变细胞功能”这个突破性的进展,在他们看来,大有可为。
两人联名发表论文,称找到mRNA的“致命弱点”。这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。
然而,学界和市场,却给他们泼了很多盆冷水。
考里科和韦斯曼拿着他们的mRNA技术项目,纷纷向各大基金委申请研究经费。项目审核小组却不认为mRNA是很好的治疗方案,将他们的申请扔在了一旁。
投稿各大一流科研期刊也杳无音讯。只有《免疫学》勉强刊发,但没有太多人关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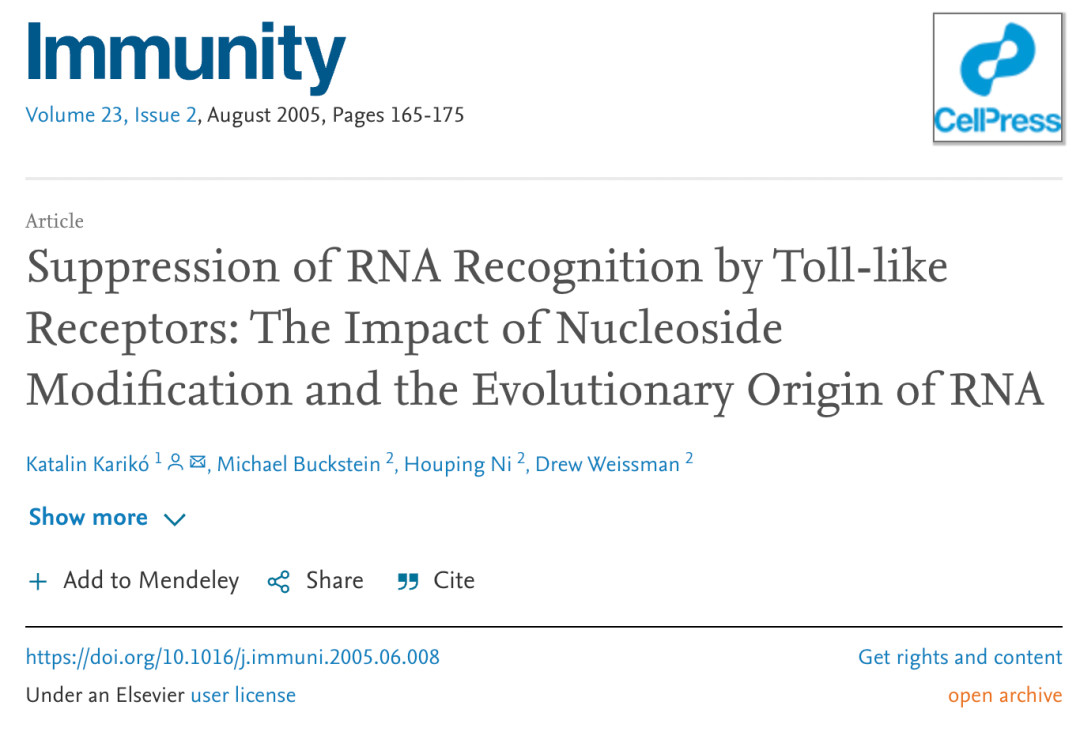
考里科和韦斯曼还是要大干一场。他们继续在实验室,埋头精进。他们成功完成了在猴子身上的活体实验。进一步证明,mRNA技术可以诱使动物选择制造蛋白质。而这样的技术,或能促使人体制造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上;同时,还能用于制造疫苗。
大干一场还是黄了
2006年考里科和韦斯曼申请了第一个mRNA相关专利,成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,尝试以mRNA为基础开发药物。公司获得的美国政府小企业资助100万美元快用完了,还是没有联系到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。考里科回忆道,“韦斯曼博士联系了很多药厂和风投,但那时,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意。”公司只好关门,第一次商业尝试黄了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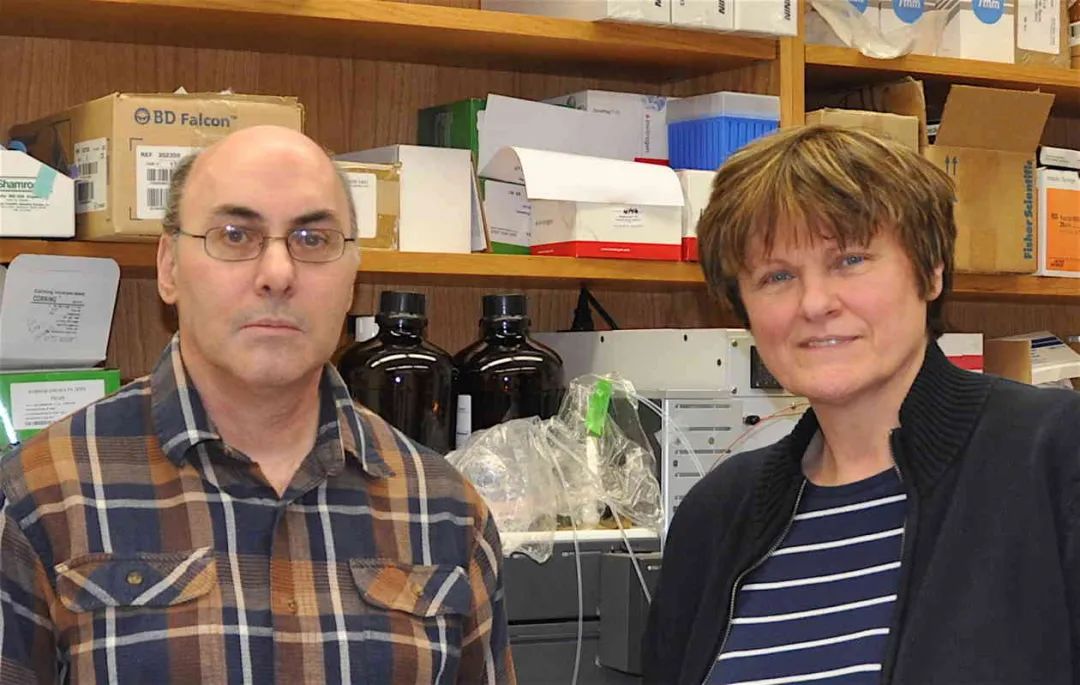
后来,成果被一个高人——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博士后Derrick Rossi注意到了,他惊叹这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。他感觉到其中巨大的商机,找到投资后于2010年成立了一家公司——莫德纳(Moderna)。在德国另一个团队也看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,也组建了一家公司——拜恩泰科(BioNTech)。这两家公司的技术,都是基于考里科和她的合作者韦斯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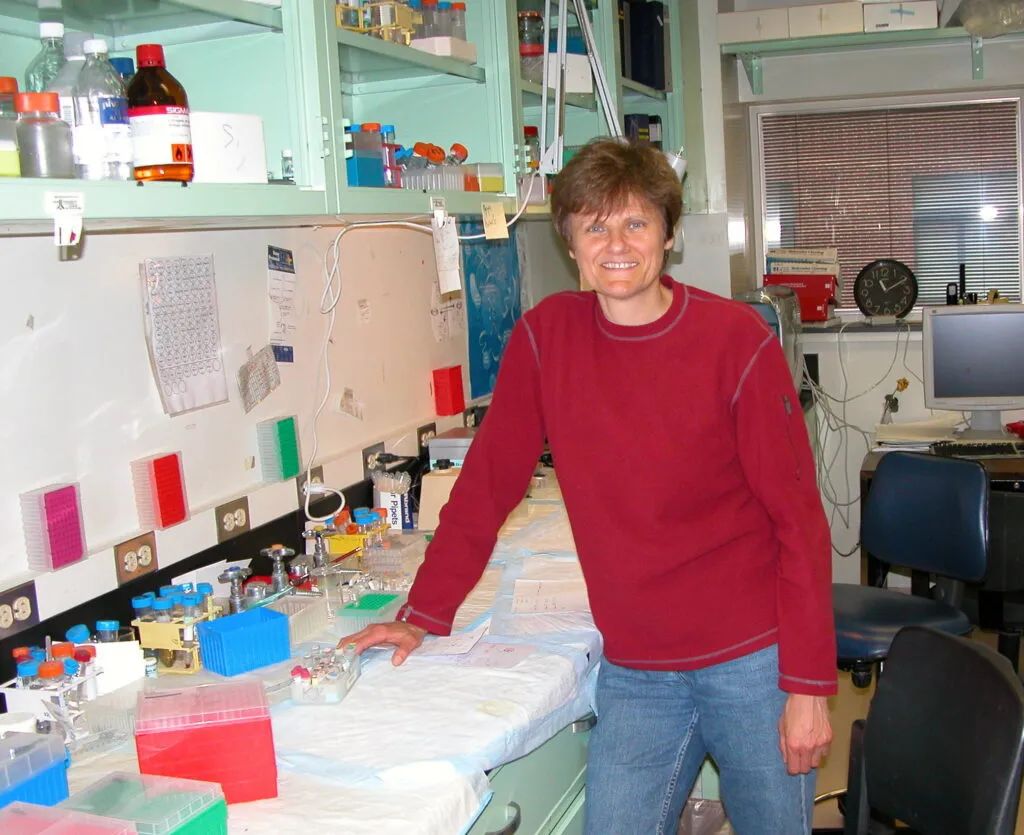
2013年,拜恩泰科聘请考里科担任高级副总裁,帮助监督mRNA工作。“得知我要加入拜恩泰科——一个找不到官网的野鸡公司,同事嘲笑我:宾大混不下去,只能去这种破地方混。”
此后8年,拜恩泰科公司发表mRNA论文150篇。虽然技术很前卫,但影响还只是局限在小圈子,直到2019年底,武汉爆发新冠疫情。

天大的机遇是新冠带来的
就在mRNA流感疫苗正进行临床试验,寨卡病毒疫苗还在开发时,2020年,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大流行。
在中国科学家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之后, 拜恩泰科用时几小时就设计出了mRNA疫苗;而莫德纳是两天内设计出了它的疫苗。
神速!
这是因为使用mRNA技术的公司不需要病毒本身来制造疫苗,只需要一台计算机来告诉科学家,哪些化学物质应该按照什么顺序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
在全球170多个疫苗项目研发比拼中,两家公司研发优势充分显现。mRNA新冠疫苗研发步入快车道。
2020年11月8日,辉瑞-拜恩泰科(Pfizer-BioNTech)疫苗研究结果出炉。

很快,莫德纳公司的疫苗结果也出来了。

拜恩泰科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布时,考里科没有狂喜。坐了 40 年冷板凳的她,第一反应是:“可算得救了!我拼命地吸气,我太紧张了,我真怕我死了……”

荣誉纷至沓来。很多学者、英国《卫报》、美国医学网站形容考里科的成就称:“或可摘得诺贝尔奖。”甚至有人说,如果今年她没能拿诺贝尔奖,那么诺奖可以关门了。
但真正让考里科开心的,是 mRNA 疫苗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。

“帮助数以亿计的人(指 mRNA 疫苗),是我从未想象过的。成为这次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,真的让我非常非常开心。”

几十年来,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“私人定制”mRNA技术的无限可能,而对于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科学家来说,这一突破不仅仅是疫苗的成功,更证明了她对mRNA治疗潜力的长期信念,mRNA技术有望在将来,为癌症、心脏病和其他传染病,提供新的治疗方法。这项技术可以为新一代的医疗和治疗方法打开大门。
传染病学家称:“这就是21世纪的科学。”
考里科已经有了新的目标。
考里科的成功,很多人眼馋她的“好运气”,是疫情给了她天大的机会。他们忘了考里科40年的苦情岁月,哪怕是在最艰难最心灰意冷的时候,她也没有放弃过mRNA。如果没有这种坚持,还会有这种“机遇”吗?
一是选择了合适的土壤。
35年后,回忆当年的决定,考里科庆幸自己离开了匈牙利,如果还呆在那,现在就是一个“不停抱怨的平庸科学家”。
二是,做自己热爱的事情,无条件相信自己。
基础研究很辛苦、很沉闷,研究者要甘于寂寞和清贫,只有真的是热爱学术研究的人,才能坚持下来。
在哈佛的一次演讲中,考里科强调她的成功“特别的依赖于失败”,因为她所研究的是未知领域,路上遭遇了无数的障碍。
但她没有放弃,她是个工作狂,经常全年无休,包括新年的那一天都在工作。有时候累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。
她享受工作,热爱研究,梦想着信使RNA技术能治疗所有的疾病。她的科研成果是惊人的,她的论文引用次数接近12000次,这是非常高的引用数字。
她的努力也激励着女儿,那个2岁时跟着她一路磕磕绊绊来到美国的苏珊。
苏珊是赛艇运动员,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,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拿到了金牌。考里科晒了很多苏珊获奖,接受采访和报道的新闻,为女儿的成就而骄傲。
坚持和天赋,考里科把这两个最好的基因,都传给了女儿。

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
有了新发现之后,对许多科学家来说,就会有发财的计划。对考里科来说,不是这样,她甚至都没打算拿300万美元分红的钱,用来买房,改善生活条件。她喜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,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。“每天都很忙。什么都不会改变。”

现在考里科和丈夫仍然住在费城外郊区一栋简陋的房子里,工作狂的考里科每天早上5点起床,跳上客厅里的划船机,用她那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,就抗原、蛋白质、细胞等问题,跟丈夫交流切磋。
66岁大器晚成的考里科的故事,也许正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最真实的写照:执着、坚持、不忘初心,40年如1日。
这个浮躁而又喧嚣的尘世中,总有人不随波逐流,不向恶俗妥协,执意自己热爱的事业,坚持不懈,无怨无悔,无视危险困苦。而这样的人,考里科是最典型的写照,她当得起我们的敬意。
致敬所有像考里科一样默默前行专注执着的科研人!

延伸阅读:
